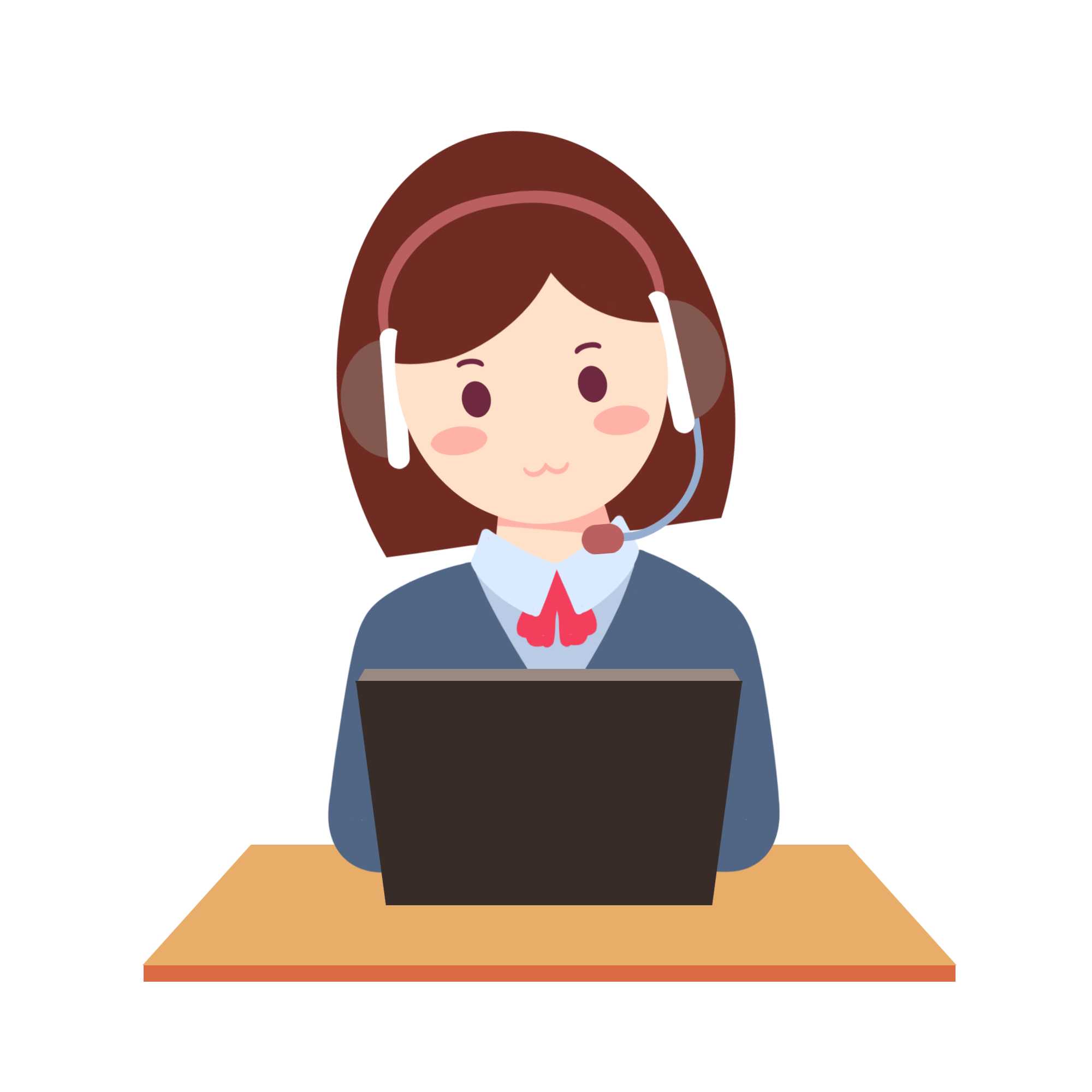6616人
6616人2021-01-20 王奇
6657阅读
暴力攻击行为是精神卫生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由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行为通常是突发性和难遇见性的,使得家属和医护人员在日常照料及护理过程中对暴力行为的评估、重视程度不足。对医疗机构来说,患者暴力行为会造成经济损失和员工离职;对医务人员来说,暴力行为会带来身体(抓伤、撞伤、咬伤、扭伤)及心理(委屈、气氛、无助、情绪低落、恐惧、自杀)的损伤;暴力行为也会造成患者与家属的情感疏离。暴力的生物学效应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包括对大脑、内分泌和免疫的影响,使抑郁、焦虑、PTSD、自杀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以及造成过早死亡[1]。如何评估、预防及治疗是精神心理科医务人员需要面对的问题。
1
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2-4](见表1)
表1 精神心理科患者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2
冲动攻击行为的生物学机制
边缘系统(杏仁核、海马、隔区、扣带回皮质和穹隆)调节攻击行为,特别是挑衅性刺激引起的攻击;下丘脑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垂体及自主神经功能,另外下丘脑中前核、外侧核、腹内侧核及背内侧核也参与了攻击行为的调控;前额叶皮层可以同时调节边缘系统和下丘脑的输入,各种原因导致的额叶受损会导致冲动攻击行为的增加[3]。杏仁核/下丘脑/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在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发生中有重要意义[5](图1)。
在各种神经递质、神经内分泌和神经肽类物质中, 5-羟色胺不足、催产素水平的下降、乙酰胆碱减少, 而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增加, 以及谷氨酸/γ-氨基丁酸系统活性的不平衡则有可能会发生冲动攻击行为[6]。
(图1)
与冲动攻击行为有关的神经环路。杏仁核(Amygdala)→下丘脑(Hypothalamus)→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被认为介导了反应性攻击行为。这条通路的激活部分取决于强化决策(Reinforcement-based decision making)所涉及的脑区,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背内侧额叶皮质(dmFC)和前岛叶皮质(AIC)。vmPFC对识别动作和目标的价值非常重要,dmFC通过获取的信息影响决策,部分通过AIC来执行。
3
暴力行为的评估
对暴力行为的评估具有以下作用:(1)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暴力倾向;(2)提高暴力行为发生的可预见性;(3)降低暴力行为的发生率;(4)规范并完善暴力行为的管理。暴力行为评估工具包括:(1)行为特征评估工具:布罗塞特暴力风险评估量表(BVC)、外显攻击行为量表(OAS)。(2)结合患者既往和当前特征的评估工具:攻击风险筛查量表(V-Risk-10)、暴力历史-临床-风险评估量表-20(HCR-20)。(3)人格特质评估工具:冲动量表(BIS-11)、冲动-预谋性攻击行为量表(IPAS)[7]。
值得一提的是,暴力行为史是预测未来暴力行为的最佳指标。然而找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询问暴力史往往比较困难,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询问暴力行为。这里,本文介绍了《麻省总医院精神病学手册》中暴力行为评估的结构化访谈条目。
表2 暴力行为的评估
4
对暴力风险患者的干预
目标:减少伤害工作人员和自己的风险,推动诊断过程。
暴力行为的急性处理包括非强制性干预和强制性干预。非强制性干预:包括口头和行为干预技术,例如用温柔、非对抗的语调谈话,提供给患者安静的并且有方便出口的房间。CBT在冲动暴力行为的干预中显示出了较好的效果[8]。如果强制性干预无法缓解攻击情形,就应该选择强制性干预措施,如强制隔离、躯体限制或使用镇静药。
快速镇静的目标包括:减少患者痛苦;保持环境安全,减少伤害他人的风险;不对患者造成伤害(使用安全方案,并且监护躯体健康)。快速镇静药物的选择见表3。
表3 快速镇静药物的选择
在快速镇静的同时,需要进行躯体监测:对于胃肠外给药患者,需要监测体温、脉搏、血压和呼吸频率。如果患者拒绝监测,应该观察是否有发热、过度镇静和一般躯体状况。如果患者处于意识丧失状态,还应该监测血氧饱和度。高剂量给药时,特别应该注意心电图及血液指标检测。
5
暴力行为发生后的干预
对暴力发生后的病人要积极进行心理护理, 让病人讲述冲动原因和经过, 以便进一步制定防范措施。以尊重、关心的态度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适当满足其合理要求, 帮助病人了解自己的病情, 以利于缓解不良情绪, 增进自控力。同时, 针对病人的个性、品德给予健康教育。对进行保护性约束的病人及时进行评估, 及时解除约束。
6
总结
精神心理科患者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较多、发生率较高、危害性较大, 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暴力行为的急性处理包括非强制性干预和强制性干预,对于快速镇静治疗的患者,需要进行躯体监测,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暴力行为的发生机制目前尚未明确,仍需未来深入分析,以开发出潜在的生物学治疗靶点。
7
参考文献
[1]Rivara F, Adhia A, Lyons V, et al. The Effects Of Violence On Health[J]. Health Aff (Millwood), 2019, 38(10): 1622-1629.
[2]Witt K, van Dorn R, Fazel S. Risk factors for violence in psycho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of 110 studies[J]. PLoS One, 2013, 8(2): e55942.
[3]TheodoreA.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ndbook of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 6th ed: Saunders/Elsevier, 2010.
[4]Chan B, Shehtman M. Clinical risk factors of acute severe or fatal violence among forensic mental health patients[J]. Psychiatry Res, 2019, 275: 20-26.
[5]Blair RJ. The Neurobiology of Impulsive Aggression[J]. J Child Adolesc Psychopharmacol, 2016, 26(1): 4-9.
[6]王中刚. 精神障碍冲动攻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特征[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1, (4): 221-223.
[7]陈明妮. 精神科暴力行为及其评估工具的国内应用进展[J]. 护理研究, 2017, 31(6): 2188-2191.
[8]Lee AH, DiGiuseppe R. Anger and aggression treatments: a review of meta-analyses[J]. Curr Opin Psychol, 2018, 19: 65-74.
[9]Hirsch S, Steinert T. The Use of Rapid Tranquilization in Aggressive Behavior[J]. Dtsch Arztebl Int, 2019, 116(26): 445-452.

好心情健康

好心情健康

好心情健康

好心情健康

好心情健康

好心情健康
扫码关注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