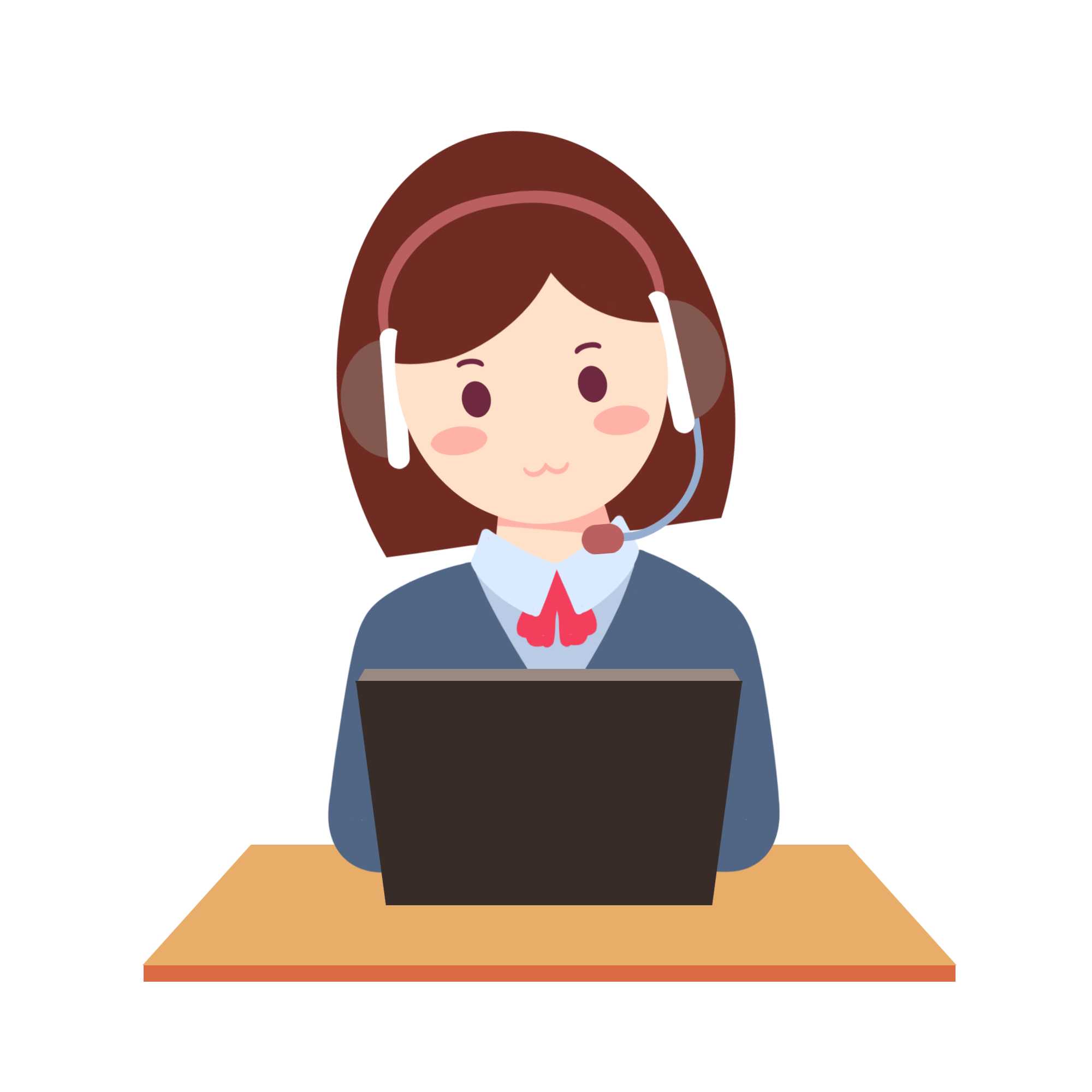10441人
10441人最近,我在门诊接触到了几个中学生,他们处在花季般的年龄,本应该朝气蓬勃、阳光积极,但是却被抑郁的情绪笼罩。他们中,近期或者1年内都有实施过自伤,有的是用刀片割腕,有的是用烟头烫自己,有的是扇自己耳光。
一个女高中生DK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高高瘦瘦,长得很清秀,比较腼腆。虽然天气炎热,她还是穿着一身长裤长袖。在诊室里她总低着头,显得心事重重,时不时用手把袖子往下拉,像是在遮盖什么。在建立起关系后,DK向我吐露了心声。由于车祸,她从小便失去了父亲,由母亲一人把她拉扯大。母亲没什么文化,开了一家早餐铺,起早贪黑,有时候会受到同行排挤、打压。母亲性格特别要强,从小对她就特别严厉,希望她以后出人头地,不要像自己一样被别人瞧不起。母亲对DK成绩上的要求几乎非常苛刻,每次考试必须班级前五名,否则DK就会受到谩骂甚至体罚。DK小学和初中时成绩很好,但是进入高中以来,成绩排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班级末尾。
近半个学期以来,DK心情特别压抑,身上难受,好像有一口气憋在心里;一到晚上莫名其妙就想哭,常常失眠。她自己在网上做了个心理评估,显示是重度抑郁。她不止一次的告诉母亲自己难受,但是母亲认为她就是作、不听话、叛逆,每次都会拿死去的父亲对她说教,并且反复强调自己有多累、多辛苦,这让她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母亲争吵时,母亲还会说出“难受了就不要上学了,上街要饭去”、“不想活了就去死”、“贱骨头”这些侮辱性的话。一说到这里,DK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但是很明显能感觉出来,她强忍着让自己不哭出来。
DK拉起了自己的袖子,在手腕处可见深深浅浅的刀割伤痕。DK割手腕已经有5次了,她是得到了自己闺蜜的“指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闺蜜是我科另一位医生的患者),希望以此吸引母亲的关注。但是当她看见母亲起早贪黑忙碌的身影时,她忍住了没说。后来几次,她感觉用刀划手让自己如释重负,甚至是一种解脱、一种救赎。她喜欢那种感觉。这次来诊,是因为伤口被母亲发现。
最后,我给DK下了抑郁状态的诊断,建议她服用舍曲林并接受心理咨询。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是近年来心理学和精神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孩子们真的“伤不起”!非自杀性自伤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社会功能,并显著增加自杀的发生[1]。以下总结了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定义、流行病学、自伤原因、临床特点、危险因素、发病机制、评估、诊断及干预,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是指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对身体表面造成的伤害,这种行为不被社会所认可。而自杀(Suicide)是指因为社会心理冲突而产生的一种蓄意终止自己生命,有目的、有计划的自我毁灭行为。
据国外调查显示,自伤行为在一般人群中的发生率约为4%,在临床样本中约为21%;在一般青少年中的发生率为14%~56%,在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临床样本中为82.4%[2]。根据DSM-IV,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中符合轴I诊断:外化障碍性(62.9%),内化性障碍(51.7%),物质滥用(59.6%);符合轴II诊断(67.3%)[3]。值得一提的是,双相情感障碍青少年中50.9%存在终身非自杀性自伤,在这些人群中,女性较多,年龄较小;被动死亡意愿、主动自杀观念、自杀未遂发生率较高的患者,更可能被诊断为双相二型;近期可能有抑郁发作、惊恐障碍、恐怖症、广泛性焦虑或PTSD;不太可能有终身ADHD[4]。
主要有以下原因:应对痛苦、对父母或亲人施压、惩罚自己、惩罚他人、追求麻木感、寻求感官刺激、避免自杀(摆脱自杀观念)、维持或试探界限[5]。

(1)行为特点: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人群中,选择一种自伤方式比例约为42.3%,选择两种、三种自伤方式者各占28.8%、13.5%。最常见的自伤方式为用刀割(71.2%),其次为用力抓(32.7%),此后依次为击打自己(26.9%),干扰伤口的愈合(19.2%),咬(15.4%),烧灼(13.5%),在粗糙的表面上摩擦皮肤(13.5%),在身体上雕刻(9.6%),用针扎(7.7%),吞咽危险物品(7.7%),拽头发(5.8%),拧(3.8%)等[6]。
(2)心理特点[7]:
不论根本诱因是什么,这些诱因都通过情绪的变化来引发自伤行为。
自伤行为可以追溯到童年期的经历,强调早期诱因对引发自伤行为的作用。
自伤行为是个体对环境不良或自身不适状况的应对或反馈方式。
后期的负性事件强化导致自伤行为的重复发生。
(3)伤口特点:
伤害的区域一般是利手所到达的区域;划痕、切口或擦伤的伤口特点:均匀低强度、外观相似、伤口拉长、成组、平行(如下图所示)。

人口学因素:女性;青少年;无业;独自生活
家庭因素:家庭健康问题;父母一方或双方有精神压力;父母和孩子有冲突
精神疾病/症状:焦虑障碍;抑郁;无助;攻击性、外化行为问题;B类人格障碍(反社会型、边缘型、表演型、自恋型);进食障碍;内化行为异常;情绪控制问题;物质滥用
童年期虐待:身体上的忽视和虐待;情感忽视和虐待;性虐待
非自杀性自伤和自杀:非自杀性自伤病史;自杀观念和自杀未遂病史;暴露于自杀行为(朋友/熟人/亲属)
(1)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的神经发育模型(见下图)

神经发育模型强调了”近端和远端因素”。远端因素(A)影响神经发育,包括基因、环境、父母教养和青年因素。这些远端因素发生于儿童期到青年期。
图B显示了与自杀(绿色)和非自杀性自伤(紫色)的脑环路,二者都涉及的脑区为黄色。PCC:后扣带回皮质;ACC:前扣带皮质;vPFC:腹侧前额叶;AI:丘脑间粘合。
图C:应激,特别是人际压力,会使远端神经标志物增加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
急性应激可能直接影响大脑,同时破坏自上而下的皮质过程,这些过程与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面向未来思维(future-oriented thinking)有关,最后导致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
慢性应激会影响调节唤醒、接近行为的边缘系统。
对部分人来说,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脑功能连接的破坏,会减缓思考到行为的转变。
急慢性应激还会导致一些负面情绪,导致自杀或非自杀性自伤。
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认为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的性别差异与脑神经环路有关。非自杀性自伤的观念和行为在女性(红色)中更为常见,而男性(蓝色)相对较少。同样,女性自杀观念和行为的风险也比男性高。跨性别少年的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也占有一定比例。
(2)内源性阿片肽和非自杀性自伤
内源性阿片肽调节成瘾和疼痛行为。非自杀性自伤可以导致内源性阿片肽的释放,进而缓解自伤行为给本身带来的疼痛,并可以增加愉悦及欣快感,进而可能导致自伤行为的重复出现。有研究显示,使用阿片类物质拮抗剂纳洛酮或纳曲酮,均可降低非自杀性自伤的发生率[10]。
(3)自伤→自杀的心理机制(见下图)

通常情况下,多次自杀未遂者会在短期内通过自残方式来缓解负性情绪。但是从长期来看,自残行为会增加负性情绪,成为一种压力源。随后,自杀可能会取代自残来调节负性情绪。例如,一项关于青少年自杀的研究显示,相对与自杀观念者来说,自杀未遂者在自杀行为后不太表现出愤怒[11]。
(1)自残功能性评估(FASM)——结构化访谈问卷:问卷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自伤行为清单(如割伤、烧伤、故意打自己等),另一部分包括22个自伤行为的动机清单,如情绪管理、人际关系、自我惩罚等功能。
(2)自我伤害想法和行为访谈(SITBI)——结构化访谈问卷:由5个模块组成: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姿态、自杀企图、非自杀性自伤。
(3)蓄意自伤问卷(DSHI):用于测量自伤的频率、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自我伤害行为的类型。
(4)贝克自杀观念量表(BSI):测量严重程度,共21组题目,操作简单,应用广泛。
(5)自伤问卷(SIQ):测量自我伤害行为的频率、类型和功能,以及它们与有童年不良经历史的关联。
(6)自我伤害行为问卷(SHBQ)——开放性临床访谈:包括4部分:了解受试者的蓄意自我伤害行为;询问自杀尝试;询问自杀威胁;询问自杀想法。
在DSM-V第三部分《新出现的量表及模式》——“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状况”中提到了非自杀性自伤的诊断标准,如下:
A:在过去1年内,有5天或更多时间,个体对躯体表面的故意伤害,包括可能诱发出血、瘀伤或疼痛(如切割伤、灼伤、刺伤、击打、过度摩擦)。
B:个体从事自我伤害行为有以下预期中的1个或更多:①从负性感觉或认知状态中获得缓解;②解决人际困难;③诱发正性的感觉状态。
C:这些故意的自我伤害与下述至少1种情况有关:①在自我伤害行动的不久前,出现人际困难或负性的感觉或想法,比如抑郁、焦虑、紧张、愤怒、广泛的痛苦或自责;②在从事该行动前,有一段时间沉湎于难以控制的故意行为;③频繁地想自我伤害,即使在没有采取行动之前。
D:该行为不被社会所认可(例如体环、纹身、作为宗教或文化仪式的一部分),也不局限于揭疮痂或咬指甲。
E:该行为或其结果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妨碍人际、学业或其他重要功能。
F:不仅仅出现在精神病性发作时、谵妄、物质中毒,或物质戒断时。在有神经发育障碍的个体中,该行为不能是重复的刻板模式的一部分。该行为不能更好的用其他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所解释。
(1)非自杀性自伤的处置流程(见下图)

(2)非自杀性自伤的管理
①探讨实施自伤的原因。
②自杀风险的评估。
③避免渲染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性及重要性:大部分自伤者并非由自杀冲动所驱使,医生的过度反应可能会无意中向他们传递一种信息,即自伤是维持他人对自己关注的有效方式,进而强化他们在痛苦时以此方式寻求支持的行为。过度反应也无助于患者理解及应对自伤行为背后的原因。
④避免接触到致死方式:避免让他们接触到枪械、锐器、药物、可能导致窒息的物件及家居中的潜在毒物,这样可以降低自伤和自杀风险。需要反复询问他们是否获取了新的工具,并且倾听他们是否有未主动告知的相关信息。
⑤完善安全计划:安全计划包括危险信号清单(情感、行为和意志等)、应对策略(散步、运动、兴趣爱好和社交等)、24小时危机援助热线、急诊、精神科医生的联系方式等。
⑥共情理解。
⑦注意反移情:重视反移情,特别是在自杀评估中。咨询师的焦虑和恐惧会放大这个来访者会自杀的可能性,忽视了他所收集了临床信息,忽视了来访者的保护资源。因此可能造成过早和过度的介入。
(3)2015年德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学会指南建议
对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的处理达成共识
培养接受治疗的动机
心理健康教育
识别诱发或使非自杀性自伤持续存在的因素
教患者行为矫正策略和解决冲突的技巧,以应对自我伤害的冲动
对存在精神障碍的患者进行处理
(4)201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皇家精神病医师学会故意自我伤害管理临床实践指南
培养改变的动机
保持冷静
强化正性情感
关注睡眠问题
(5)2011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指南——长期管理的一般注意事项
培养信任、支持和参与的关系
意识到与自我伤害有关的耻辱与歧视,不做评判
确保他们充分参与到治疗和护理决策中
尽可能培养自主性和独立性
尽可能保持治疗关系的连续性
确保自我伤害的有关信息及时传到治疗团队中的成员
(6)心理干预
大量证据表明,认知行为疗法(CBT)、辩证行为疗法(DBT)和心理化基础疗法(MBT)治疗非自杀性自伤有效[17-19]。
(7)药物干预
根据所伴随的精神症状群,可以选择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和阿片受体拮抗剂等药物。药物治疗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循证医学证据仍然不足;药物治疗应该与心理治疗联合使用,不建议单一用药。

参考文献:
[1]Vega D, Sintes A, Fernández M, et al. Review and update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who, how and why?[J]. Actas Esp Psiquiatr, 2018, 46(4): 146-155.
[2]吴名道, 毛绍菊, 唐寒梅, 等. 非自杀性自伤与边缘性人格障碍关系的研究概述[J]. 2017, 044(003): 486-489,506.
[3]Nock MK, Joiner TE, Gordon KH,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adolescents: diagnostic correlates and relation to suicide attempts[J]. 2006, 144(1): 65-72.
[4]Scavone, A., Timmins, et al.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correlates of non-suicidal self injury in adolesc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J]. 2015, 17(Suppl.1): 104-105.
[5]Joshi KGJCP. Caring for adults who engage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J]. 2021, 20(1): 11,45.
[6]林明婧, 厉萍, 精神医学杂志 卢庆华.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研究现状[J]. 2018, 031(001): 67-70.
[7]马小卫, 赵斌. 以功能性分析为导向的自伤行为解释模型研究综述[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14, (19): 4-8.
[8]Plener PL, Kaess M, Schmahl C,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dolescents[J]. 2018.
[9]刘珍珍, 汪心婷, 刘贤臣, 等. 自杀行为暴露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纵向研究[J]. 2019, 40(12): 1573-1577.
[10]Bresin K, Gordon KHJN, Reviews B. Endogenous opioid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mechanism of affect regulation[J]. 2013, 37(3): 374-383.
[11]Hilario BF, Roberto FF, Laura C, et al. The Addictive Model of Self-Harming (Non-suicidal and Suicidal) Behavior[J]. 2016, 7(4): 8.
[12]刘婉, 万宇辉, 陶芳标, 等.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估方法研究进展[J]. 2016, 32(4): 478-481.
[13]Halicka J, Kiejna A.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and suicidal: Criteria differentiation[J]. Adv Clin Exp Med, 2018, 27(2): 257-261.
[14]Plener PL, Fegert JM, Kaess M,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dolescence: a clinical guideline for diagnostics and therapy][J]. Z Kinder Jugendpsychiatr Psychother, 2017, 45(6): 463-474.
[15]Carter G, Page A, Large M, et al. Roya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deliberate self-harm[J]. Aust N Z J Psychiatry, 2016, 50(10): 939-1000.
[16]Kendall T, Taylor C, Bhatti H, et al. Longer term management of self harm: summary of NICE guidance[J]. Bmj, 2011, 343: d7073.
[17]McCauley E, Berk MS, Asarnow JR, et al. Efficacy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for Adolescents at High Risk for Suicide: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Psychiatry, 2018, 75(8): 777-785.
[18]Ougrin D, Tranah T, Stahl D, et al.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for suicide attempts and self-harm in adolescen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15, 54(2): 97-107.e102.
[19]Rossouw TI, Fonagy P. Mentalization-based treatment for self-harm in adolesc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12, 51(12): 1304-1313.e1303.
[20] Plener PL, Libal G, Fegert JM, et al. Psycho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J]. 2013, 32(1): 38-44.

本内容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作为疾病诊断及治疗依据,请谨慎参阅 本内容版权归好心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好心情健康

好心情健康

好心情健康

空谷幽兰
扫码关注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