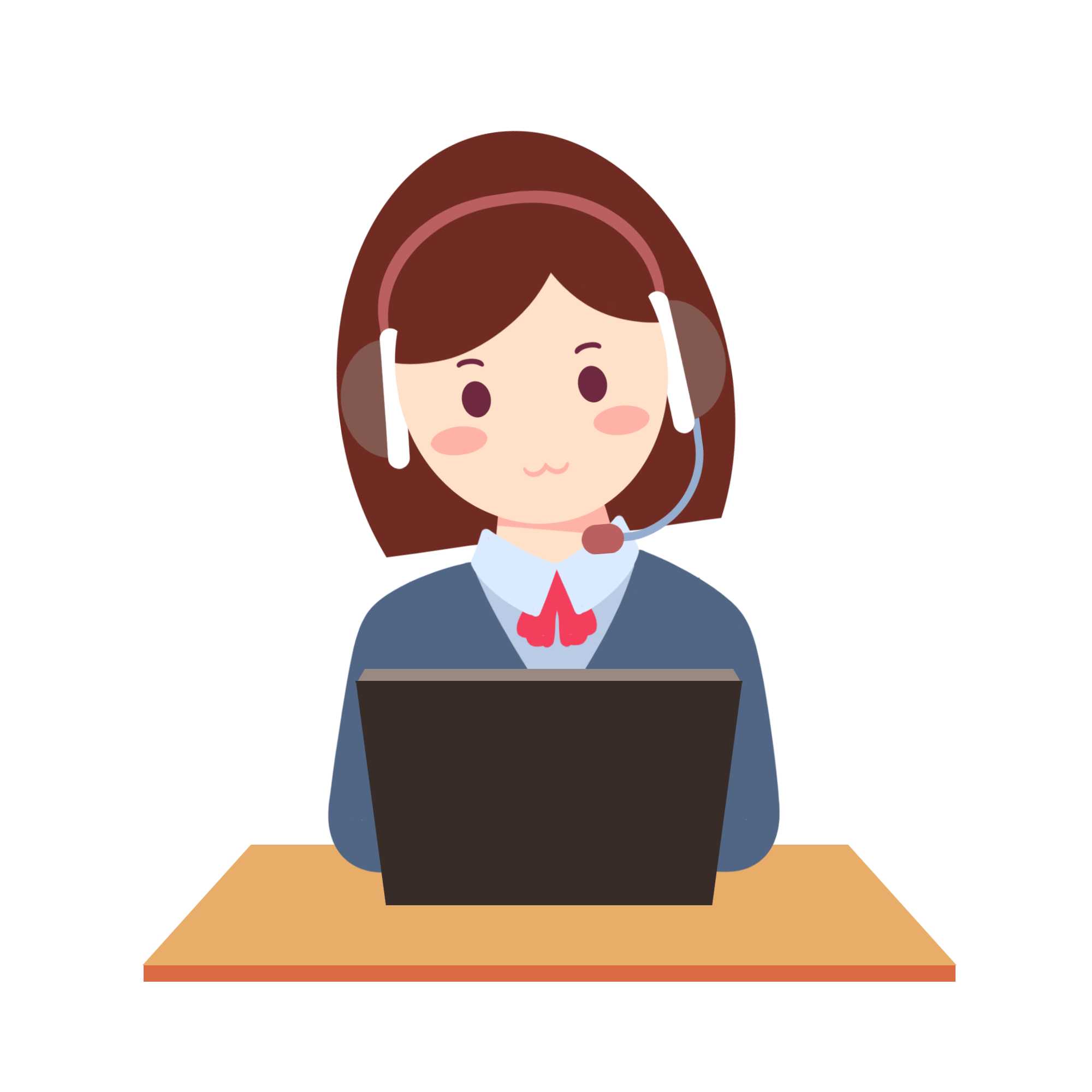9202人
9202人文 |苗国栋
我在门诊工作中,很留意病人和病人家属,尤其是病人父母的言语表达方式及内容、他们的情绪状态和面部表情,发现在他们言语表达方式和内容与情绪状态及表情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作为一般规律,我的大多数门诊病人的病情在治疗开始后都会趋于稳步改善。有鉴于此,我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开场白基本相同:“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变化?”病人家属给我的回答尽管因人而异,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那些诊断为焦虑、抑郁的青少年患者的父母,往往首先告诉我,他们的子女哪些症状无改善,出现了哪些药物副作用,并担忧他们病人的这些问题是难以控制或无法治愈的,基本不会主动提及病情改善的信息。在病人父母陈述过上述内容后,多数情况下我不会立刻回应,而是会期待地望着对方,希望他们继续反映情况,尤其是希望听到病情改善的信息。此时,他们往往会打住,纳闷地看着我,不知道继续说什么。看着他们搜肠刮肚地继续找患者没有改善的症状及可能的药物副反应的同时,我就会特别留意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特征及其所反映的情绪状态。
此时,我基本都会发现他们反映病情时的焦虑情绪或抑郁情绪。除了他们悲戚的面容、紧锁的眉头和一声声长吁短叹之外,他们对其子女病情变化的悲观性评估也反映了他们与情绪状态一致的认知。在他们觉得已经把自己该说的话说完之后,我会根据我的经验和对病人表现的观察发问,如睡眠有无改善,焦虑有无减轻,言语声有无增大,笑容有无增多等。病人父母多会回应称,我问到的那几个方面均有改善。接着,我会问:“为何你们不会主动告诉我病人好起来的这些现象呢?”病人父母往往因不理解我发问的目的,多会解嘲般地讪笑着说,他们没有留意,如果我不问,他们大概想不到这些方面的改善。
接着,我会解释说,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病人在我说的那些方面有所好转。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善,我就会重新审视我做出的疾病诊断是否正确,我的治疗药物是否合理。所以,我需要这方面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会征询病人本人的体验,绝大多数病人都会给我肯定的回答。
而且,在我与病人或其父母交流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更为有趣而且有点儿令人费解的现象:若是我问了开场白那样的问题,病人父母没有抢着回答时,多数病人会与其父母不同,先告诉我,他的哪些症状有了改善。然后,才会陈述自己尚未改善的问题。我猜,是患者父母相对定型的负性认知模式,妨碍了他们关注其子女们已经出现改善的现象。
在结束了与病人及其父母就病情的交流之后,我会和这些病人父母说:“我非常希望下次病人复诊时,你们先告诉我好消息,然后再告诉我那些不好的消息。”我觉得我提这样的要求不是矫情。
我的用意至少有三:
一是先告诉我好消息对病人有鼓励作用,让病人体会到家人对他的进步是在意的,他也会更在意自己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
二是引导病人在观察、感受生活时,学会以更积极的心态,形成正性认知模式。长此以往,耳濡目染,病人的认知倾向都会变得积极起来。
三是有助于病人及其父母重视人际交流中传递信息的模式,让听者有兴趣倾听、乐于倾听,也容易让听者对言说者有更好的评价,改善交流质量,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试想,任何人若听到言说者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开口就是诉苦,都会觉得遇上了“怨妇”,自然会敬而远之。
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我觉得上述道理对一般人的言语表达和人际交往或许也有意义:就像俗语语说的那样,“伸手不打笑脸人”,与人分享喜悦,是人们愿意继续交流的必要条件。

扫码关注医生